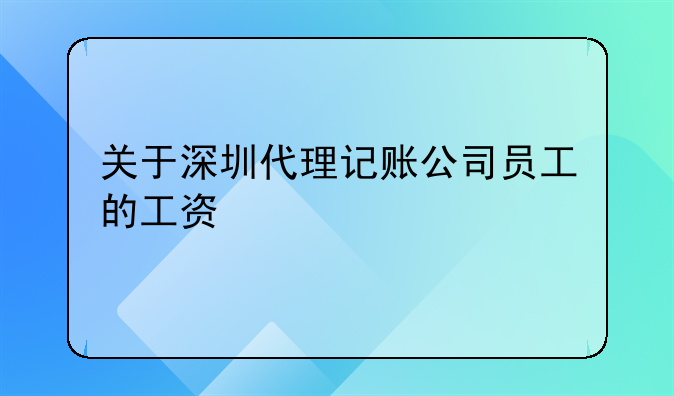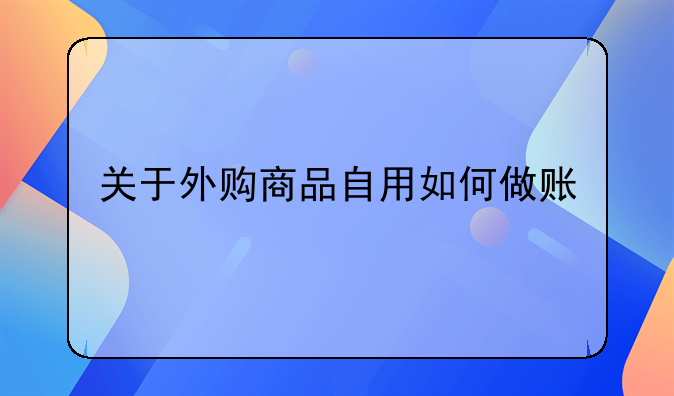咨询电话: 1317-2164-214
母亲葬礼结束后,兄弟姐妹收拾东西要走,大哥:这钱怎么算的
发布于 2025-05-06 16:48:04 作者: 顿莘莘
注册公司是创业者必须面对的任务之一。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复杂,但是只有完成这个过程,你的企业才能够合法地运营。主页将会介绍出售旧物怎么做账,有相关疑问的阅读者,那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分母
"这钱怎么算?"大哥刘长海把一本发黄的账本重重拍在桌上,眼神在我们几个人脸上逡巡。
母亲的葬礼刚结束,院子里还弥漫着纸钱的焦糊气息,混合着冬青树的苦涩。
大哥粗糙的手指摩挲着那本账本磨损的边角,仿佛在摩挲一段无法释怀的往事。
屋里一时静得出奇,连墙上那个老式挂钟的"嘀嗒"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们五兄妹聚在老家的四合院里,收拾着母亲留下的遗物。
大哥刘长海,在县城机械厂当工人,是厂里有名的铣工能手,前些年还拿过县劳模。
二姐刘淑兰,乡卫生院的护士,善良温婉,院里的老人都喜欢找她打针,说她手轻。
我排行老三,刘建国,在区供销社上班,一个不起眼的小会计,日子过得不咸不淡。
四弟刘建民,是我们家的"状元郎",考上了省城一家印刷厂的技术员,还评上了工程师。
小妹刘小梅,留在村子里教书,嫁了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小学代课老师,两人都安于清贫。
院子里的老槐树上,一只知了在不知疲倦地鸣叫,声音划破了尴尬的寂静。
"快秋分了,还有知了叫呢。"二姐低声嘀咕,像是在逃避屋里那股压抑的气氛。
母亲七十八岁,走得很安详。医生说是"老年心衰",没受太多罪。
最后几年,我们几个轮流接她住,每家都备了专门的房间,叫"奶奶屋"。
我至今记得母亲住在我家那段时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非要帮着做家务,说是"闲不住"。
"坐着不是浪费粮食吗?"母亲总爱这样说,一辈子勤劳惯了,不知道什么叫"享福"。
每次吃饭,母亲总是先给孙子孙女们夹菜,自己却只吃咸菜拌饭,说荤腥"吃不惯"。
我们谁家都有本记账的小本子,记着给母亲买什么药、挂什么科、吃什么补品,甚至坐公交车的两毛钱都一一记下。
这在当时并不稀奇,工薪家庭过日子,都精打细算,尤其是那会儿"下岗潮"刚起,谁都怕自己成了"富余人员"。
"咱们各家条件不一样,花销自然不同。"大哥翻着账本,语气有些生硬,"我看按比例分摊比较公平。"
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窗外,一阵秋风掠过,卷起几片黄叶,打着旋儿落在院子中央那棵老槐树下。
母亲的房间还保持着她生前的样子,那张木板床上叠着整齐的"万字格"被褥,一个旧式的搪瓷茶缸放在床头柜上。
墙上挂着全家福,那是四弟结婚时照的,母亲站在中间,憨厚地笑着,眼角的皱纹像一把小扇子。
"长海,娘都走了,还算这个做什么?"二姐淑兰擦着眼泪说,她性子最软,平日里对大哥言听计从。
"怎么不算?"大哥抬起头,眼里闪着倔强的光,"要是不算清楚,心里那个疙瘩就解不开。"
我沉默地看着这个从小拉扯我们的大哥。十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辍学进厂,硬是把我们几个拉扯大。
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深得多,仿佛生活的重担在他脸上刻下了年轮。
记得那会儿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大哥常不吃早饭,说是"不饿",其实是把定量的粮票省给我们几个。
夏天,他舍不得开电扇,说是"浪费电";冬天,他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袄,却给我们每人添置了新衣裳。
"你们记性咋恁差?"大哥翻过账本,拍了拍密密麻麻的记录,"去年娘住我家,光买降压药就花了一百多。"
他说这话时,眉头紧锁,脸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活像爹当年训人的模样。
四弟坐不住了,起身踱到窗前,点了根"红塔山",深深吸了一口。
"大哥,不是我说,你这么精细算账,像啥话?"他语气里带着不屑,"娘要是知道,不得从棺材里跳出来?"
"你懂个屁!"大哥一拍桌子,茶缸里的水都跳了起来,"你在省城当工程师,自然不在乎这点钱!"
"行了行了,别吵了。"二姐赶紧打圆场,"这事好商量,何必伤了和气?"
我看着四弟嘴角那抹嘲讽的笑,心里暗叹一口气。自从他考上大学,家里人对他都另眼相看,他也渐渐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
"大哥,你还记得吗?"二姐突然说,"小弟上大学那年,家里揭不开锅,是娘偷偷把她织毛衣的钱都给了小弟。"
那时候,村里人看不起没文化的,都说我们刘家"出了个读书人,祖坟冒青烟了"。
四弟低着头,眼圈红了。那时他考上了省城大学,全村人都羡慕,可家里连学费都凑不齐。
是母亲日夜赶织毛衣,手上的皮都磨破了,硬是一针一线攒够了钱。
大嫂从厨房端来一壶茶,摆上几个缺了口的茶杯,默默给我们都倒上。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嫁给大哥二十多年,任劳任怨,很少抱怨什么。
"娘从来不计较这些。"我终于开口,"我记得她常说,养儿防老不如积德行善。"
"就是,娘那人最大方了。"小妹附和道,"上回我要盖房子,娘悄悄塞给我五百块,让我别告诉你们。"
"五百?"大哥眉毛一扬,"她给我家添冰箱,只给了三百!"
"我娃上幼儿园,娘给凑了两百。"二姐小声说。
"我媳妇生孩子,娘给了四百。"四弟也不甘示弱。
我们互相看了看,突然意识到母亲这些年暗地里给每个子女都有资助,却谁也没告诉谁。
大哥脸色变了变,翻着账本的手停住了。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这些年,娘的退休金都花到哪去了?"大嫂突然问,"她老人家一个月一百多,也没见她买啥东西。"
屋里又陷入了沉默。是啊,母亲这些年,总是穿着几套旧衣服,舍不得买新的;吃的是最便宜的挂面和萝卜,舍不得买肉;生病了舍不得住院,说是"小病,扛扛就过去了"。
"那你说怎么算?"大哥声音发涩,"我媳妇为了照顾娘,连厂里的职称都没评上。"
四弟坐回桌前,点燃了第二根烟,语气也软了下来:"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哪个意思?"大哥冷哼一声,"你们都觉得我小气是不是?"
小妹叹了口气:"大哥,咱们别这样,今天是娘的头七,她在天上看着呢。"
院子里,广播站传来《天气预报》的音乐,然后是播音员平稳的声音:"今天全县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二十五度"
母亲生前最爱听天气预报,说是知道天气,好安排晾晒衣物和被褥。
"那我问你们,这几年谁陪娘的时间最多?"大哥声音发涩,"我媳妇为了照顾娘,连厂里的职称都没评上。"
"大哥,那你说怎么算?"四弟抬起头,眼里有些不服气,"按住的天数算?还是按花销算?"
正争执着,小妹从里屋走出来,怀里抱着一个旧布袋。"我在娘的枕头底下找到的。"她轻声说。
那是母亲最心爱的一个绣花布袋,绿底红花,年年换新绳,却一直舍不得换新袋子。
我们围上去,大哥小心翼翼地解开布袋。里面是五个小纸包,每个上面都写着我们的名字。
"这是啥时候写的?"大哥问,声音有些颤抖,"娘连小学都没念过,是谁帮她写的?"
"应该是村小学的王老师。"小妹说,"娘常去找他东西。"
最上面是一张纸条,小妹颤抖着声音读出来:"儿女们,娘知道你们都不容易。大儿要强好胜,这是救急的;二女心善,这是给孙女添嫁妆的;老三忠厚,这是给你添补家用的;四儿有出息,这是给孙子上学的;小女教书苦,这是给你修房子的。娘的一生没有大出息,能留下这些,已是幸事。你们和和气气的,就是给娘最大的安慰。"
读到这里,小妹的声音哽咽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压抑的啜泣声。我抬头看了看,连大哥那张总是绷得紧紧的脸也松动了,眼角湿润。
那些纸包里,是母亲多年来省吃俭用存下的钱,还有她亲手织的毛背心和袜子。
每个包里还有一张字条,是母亲找人代写的嘱托,字迹歪歪扭扭,却格外认真。
大哥打开自己那份,里面竟然还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背面写着:"大儿吃苦了,娘心疼。"
那照片是在县照相馆照的,大哥穿着借来的中山装,神情严肃,那会儿他刚进机械厂不久。
见到这照片,大哥再也绷不住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扑在桌上失声痛哭。
"当年,娘为了给我凑份子钱去照相,硬是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卖了。"大哥抽泣着说,"那鸡是留着过年的。"
"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二姐接过话头,"家里没钱买煤,娘就去田埂捡柴火,手冻得都裂了口子。"
"还有那次,知青张老师要回城,送了娘一件毛衣。"我也回忆起来,"娘舍不得穿,拆了线给我们几个织了手套。"
"记得那年我发烧,娘走了十里地去镇上买药。"四弟声音低沉,"回来时天都黑了,她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
"娘常说,'穷家的孩子早当家'。"小妹眼中含泪,"可她自己却从来舍不得享福。"
我想起母亲佝偻的背影,想起她布满老茧的手,想起她总是说"我不累"的笑容。
她怕冷却从不多穿,说是浪费;她舍不得坐公交,宁可走上一个小时;她从不买新衣服,却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准备了压岁钱。
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无私的母爱,什么是平凡人的伟大。
窗外,太阳渐渐西沉,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极了母亲望着我们远去的目光。
大院里,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评书的声音,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不时传来。
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仿佛母亲还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一边择菜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水浒传》。
大哥忽然站起身,走到火盆旁,把那本账本扔了进去。"娘这辈子没白活,咱们做儿女的,怎么能算计她的付出?"他声音哽咽。
火苗舔舐着账本的纸页,那些数字和日期慢慢化为灰烬,就像母亲的一生,不留痕迹地消融在岁月长河中。
"要是娘知道我为了这点钱跟你们争,得多心疼啊。"大哥自责地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大哥,谁还没个想不开的时候?"我安慰道,"咱娘常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二姐打开自己的纸包,里面是两百块钱和一个小绒布袋。袋子里装着一枚金戒指,是母亲的嫁妆,传说是太奶奶留下来的。
"这是娘唯一的值钱东西了。"二姐哽咽着说,"她老人家连热水袋都舍不得买一个。"
四弟的包里也有钱,还有一本存折,上面是母亲这些年存的"教育基金",足足有八百多元。
"我孩子才上幼儿园啊。"四弟红着眼圈说,"娘这是准备让我娃一直读到大学呢。"
小妹的包里除了钱,还有一副手套,是母亲亲手织的,针脚细密,一看就费了不少工夫。
"去年冬天我回来,跟娘说手冷。"小妹抚摸着那副手套,"没想到她记在心上了。"
我的包里有三百元,还有一个小药瓶。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几粒红枣和花生,还有一张纸条:"建国,你胃不好,多吃些枣和花生补补。"
这些年,我为了供销社的账目,经常加班熬夜,落下了胃病。母亲每次来我家,总是变着法子给我做养胃的食物。
"我提个建议。"我说,"娘留下的钱,咱们不分了,捐给村小学,设个'孙氏助学金'那些像咱们小时候一样困难的孩子。"
大家都点头赞同。小妹又说:"老宅也别卖了,收拾收拾,做个'留守儿童之家',让孩子们放学有地方去。娘生前最心疼那些小孩子。"
"我记得娘常说,'家里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四弟深有感触地说,"当年要不是她坚持,我哪能考上大学?"
"就这么定了。"大哥拍板,"以后每年咱们轮流回来,看看那些孩子,也算是替娘尽尽心。"
大嫂默默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饭。不一会儿,锅碗瓢盆的声音响起,伴着葱花下油锅的香气。
"来,咱们帮大嫂一起做饭。"二姐招呼着,"娘走了,咱们更得和和气气的。"
我和四弟去院子里的水井打水,小妹在灶间生火,大哥劈柴,一家人忙碌起来,默契十足。
院子里的老水井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井台上的石板被磨得锃亮,那是几代人挑水时留下的痕迹。
井水清凉甘甜,我用老式的铁勺舀了一勺,递给四弟。他喝了一口,感慨道:"家乡的水,还是这个味道。"
晚饭很简单,却也丰盛:大嫂炒的番茄炒蛋,二姐做的醋溜白菜,小妹蒸的南瓜饼,还有我和四弟从镇上买回来的熏鱼。
"来,先给娘盛一碗。"大哥把最先盛好的米饭放在中间的位置上,那是母亲生前常坐的地方。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像过去无数个团圆的日子,只是少了母亲那张慈祥的面孔。
"娘要是在,肯定催我们快吃。"二姐笑中带泪,"还会说'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对,还会说'别光顾着说话,多吃点'。"四弟也笑了。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笑声渐渐盖过了悲伤。
母亲好像就坐在我们中间,欣慰地看着她的儿女们和睦相处,那是她一生最大的心愿。
傍晚时分,我们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着夕阳西沉。树上的知了还在鸣叫,仿佛讲述着一个关于母爱的古老故事。
四合院的砖墙被夕阳染成了金色,远处的田野里,稻子泛着金黄,秋风送来一阵阵稻香。
"咱娘这一辈子,算过太多人情世故的账,却从来没算过子女的账。"大哥忽然说,"这才是最值钱的人情味啊。"
"娘走得那天,还牵挂着院子里的韭菜。"小妹轻声说,"说是'割了好发新芽'。"
二姐拿出一个旧布包,里面是母亲平日里用的针线包、老花镜和一本《农家历书》。
"咱们一人一件,留个念想吧。"她分发着,"娘的东西不多,却是她用了一辈子的。"
我拿到了那本《农家历书》,扉页上有娘歪歪扭扭写的几个字:"看天种地"。
那是她一生的智慧,也是她留给我们的最朴素的处世哲学。
"娘走了,咱们更要好好的。"大哥说,"不能让她在九泉之下还惦记着。"
"娘有我们几个儿女,没有白活一场。"四弟说,声音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
夜幕降临,星星点点亮起,像极了母亲看我们时眼中的光芒。
老屋四周的青草味、泥土香,还有柴禾的烟火气,都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和安心。
这就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用一生的辛劳和爱编织的温暖巢穴。
"我常想啊,咱娘这一辈子,没念过书,没出过远门,却把五个孩子都拉扯大了,这比当官发财都难。"大哥感慨道。
我们默默点头。的确,母亲那一代农村妇女,承受着生活的全部重担,却从不喊苦喊累。
她们的人生没有波澜,却又何其壮阔;她们的故事平凡无奇,却又感人至深。
我看着手中那张发黄的照片,上面是年轻时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我,笑得那么温暖。
我终于明白,真正的亲情,从来就不是用数字能衡量的。它没有分母,只有无限的大爱。
大爱无言,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大爱无私,如大地厚重,承载万物;大爱无价,如星辰永恒,照亮人间。
这就是母亲的爱,朴实无华,却胜过世间所有的珍宝。
在这个秋天的夜晚,在这个充满回忆的老院子里,母亲虽然离去,却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她用爱编织的那张网,让我们互相扶持,共同前行。
这,才是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我们通过阅读,知道的越多,能解决的问题就会越多,对待世界的看法也随之改变。所以通过本文,主页相信大家的知识有所增进,明白了出售旧物怎么做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