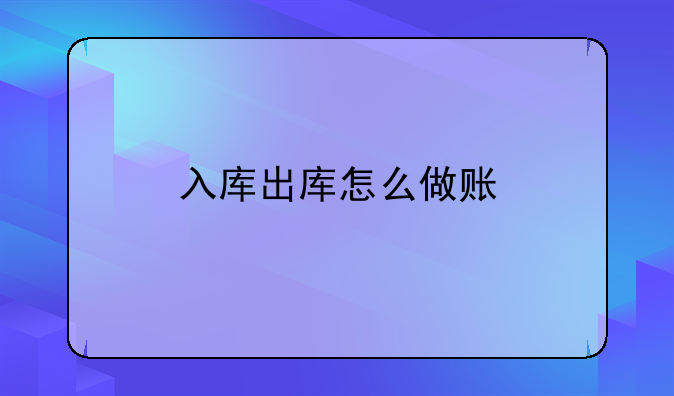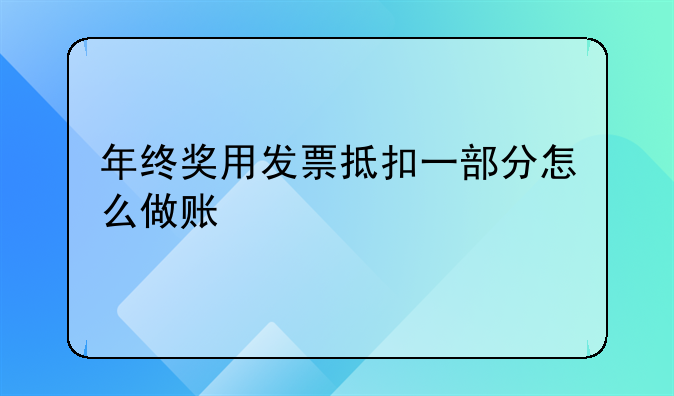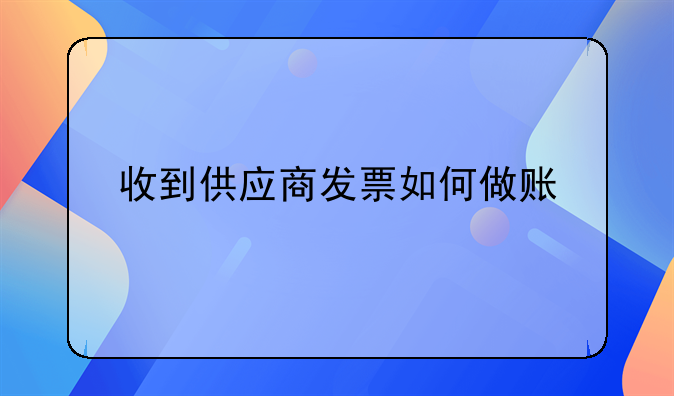咨询电话: 1317-2164-214
46年,外公的绸缎庄倒闭,遣散账房先生时,那人还回一支旧算盘
发布于 2025-12-18 01:36:03 作者: 党闳
注册公司是创业者成为合法企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通过完成这个过程,你可以获得法律保护,让你的企业更加正式和专业。接下来,主页将给大家介绍遣散费做账的相关信息。希望可以帮你解决一些烦恼。

那支磨得发亮的旧算盘递回来时,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外公那样红着眼眶的模样!
民国三十五年的春末,巷口的梧桐刚发新芽,绿得嫩生生的,风一吹就晃悠。我那时才八岁,总爱蹲在绸缎庄的门槛上,看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听账房先生老周叔拨算盘的声响。
绸缎庄的门脸是朱红色的,两扇木门上的铜环被摸得锃亮,推门时会发出 “吱呀” 一声脆响,像老伙计打招呼。门里的货架摆得整整齐齐,绫罗绸缎堆得像小山,红的似霞,绿的如翠,还有带着暗纹的锦缎,在阳光下会泛出细碎的光。外婆总说,这些料子是外公的命根子。
外公年轻时走南闯北,从杭州进货,挑最好的绸缎运回来,在镇上开了这家 “瑞昌祥”。街坊邻里都说,外公的绸缎,颜色正,料子实,嫁女儿、做寿衣,都愿意来这儿挑。
老周叔是绸缎庄的账房先生,跟着外公快二十年了。他总坐在靠窗的八仙桌后,桌上铺着青灰色的毡子,算盘就摆在正中央。那算盘是紫檀木的,框子被摩挲得发亮,算珠是黑色的,圆润光滑,每一颗都带着老周叔手指的温度。
我总爱凑到老周叔身边,蹲在他脚边看他拨算盘。他的手指又粗又短,指节突出,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指尖上有一层厚厚的茧子,是常年拨算盘磨出来的。
“小丫头,别在这儿捣乱,小心你外公敲你脑袋。” 老周叔拨着算盘,眼睛盯着账本,嘴里却没闲着。
“我不捣乱,我就看看。” 我扒着八仙桌的边缘,踮着脚尖看账本上的字,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像小蚂蚁,我一个也不认识。
外公这时会从后堂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匹刚到的绸缎,青绿色的,上面绣着淡淡的兰草。他走到货架前,小心翼翼地把绸缎展开,抚平褶皱。
“老周,这批货的账算好了吗?” 外公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生意人特有的沉稳。
“快了,东家,还差最后一笔。” 老周叔手里的算盘噼啪响,快得惊人,“这批杭州来的货,运费比上次贵了两成,料子价钱倒没涨。”
“运费贵了?” 外公皱了皱眉,伸手摸了摸绸缎的料子,“时局不太平,路上难走,贵点也正常。”
外婆这时会端着一壶茶从后院进来,茶盘是白瓷的,上面放着两个粗瓷茶杯。她走到八仙桌旁,把茶盘放下,给外公和老周叔各倒了一杯茶。
“天热,喝点茶解解暑。” 外婆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她总是这样,说话细声细气,却把家里和绸缎庄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老周叔停下算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咂咂嘴:“老板娘的茶还是这么香,比街上茶馆的强多了。”
“就你会说。” 外婆笑了笑,伸手拍了拍我的头,“丫头,别总蹲在这儿,地上凉,去后院玩会儿。”
后院有一棵石榴树,春末时开着火红的花,像一个个小灯笼。我跑到后院,摘了一朵石榴花,捏在手里玩。远远能听到前堂的声音,算盘声、外公和老周叔的说话声、客人的询问声,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那是绸缎庄最好的时光。
那时的日子,像绸缎一样光滑顺溜。每天清晨,外公会第一个到绸缎庄,把木门打开,将货架上的绸缎一一整理好。老周叔随后就到,背着他的旧布包,里面装着账本和笔墨,一坐下就开始对账。外婆会在家做好早饭,让我端到绸缎庄来,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碟咸菜,简单却吃得香。
客人多的时候,我会帮着递料子。有一次,镇西头的张太太来做寿衣,要挑最好的织金锦。外公亲自给她展开料子,金色的纹路在光下闪着亮,张太太摸了又摸,笑得合不拢嘴。
“瑞昌祥的料子就是好,我老婆子这辈子,就想穿件像样的寿衣。” 张太太说。
“张太太放心,这料子结实,颜色也正,保准您满意。” 外公笑着说,手里的料子被他抖得平平整整。
老周叔在一旁记账,算盘珠子噼啪响,很快就报出了价钱。张太太爽快地付了钱,临走时还夸:“东家实在,账房先生也利索,以后还来这儿。”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年。我慢慢长大,从蹲在门槛上看行人,到能帮着外婆收拾布料,帮着老周叔递账本。绸缎庄的铜环被更多人的手摸过,算盘珠子被老周叔拨得更亮,货架上的绸缎换了一批又一批,却始终堆得满满当当。
可民国三十五年的秋天,一切都变了。
先是街上的行人少了,再是来绸缎庄的客人越来越少。往日里噼啪响的算盘,变得安静了许多。老周叔常常坐在八仙桌后,对着账本发呆,手里的算盘拨了一半就停下。
外公的眉头,也一天比一天皱得紧。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整理绸缎时哼着小曲,而是常常站在门口,望着空荡荡的街道,眼神沉沉的。
“东家,这月的生意,比上月又少了三成。” 老周叔把账本递给外公,声音低低的。
外公接过账本,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在纸面上摩挲,半天没说话。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的脸上投下阴影,我看到他鬓角的白发,比以前多了不少。
外婆端着茶进来,看到两人的样子,把茶放下,轻声说:“别太愁了,时局不好,大家都紧着过日子,谁还舍得买绸缎。”
“可这绸缎庄,是我的心血啊。” 外公叹了口气,把账本放在桌上,“从一间小铺子,到现在这样,我花了二十年。”
“我知道。” 外婆拿起一块布料,轻轻抚平,“可日子还得过,总不能揪着不放。”
老周叔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拨着算盘,珠子发出单调的声响。“东家,我跟着你二十年,瑞昌祥就像我的家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跟着你。”
外公看了看老周叔,眼里有了点暖意:“老周,委屈你了。这几个月,工钱都没给你涨。”
“东家说啥呢。” 老周叔抬起头,脸上露出憨厚的笑,“我跟着你,不是为了涨工钱,是信得过你。再说,家里的日子还能过,不缺这点钱。”
可日子并没有好转。入冬后,物价涨得厉害,一袋米的价钱,比以前翻了三倍。街上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外公的绸缎庄,也快撑不下去了。
那天早上,我到绸缎庄时,看到外公正坐在八仙桌前,对着一堆布料发呆。老周叔站在一旁,手里拿着账本,脸色凝重。
“丫头,你先回家去。” 外公看到我,挥了挥手。
我没动,蹲在门槛上,看着他们。我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
老周叔把账本放在桌上,轻声说:“东家,库里的绸缎,还有不少,可没人买。运费越来越贵,进货都成了问题。”
外公点了点头,声音沙哑:“我知道。昨晚我想了一夜,这绸缎庄,怕是撑不下去了。”
老周叔身子一僵,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外婆这时也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走到外公身边:“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家里还有点积蓄,要不先垫上?”
“没用的。” 外公摇了摇头,“时局这样,就算垫上,也撑不了多久。与其到最后一无所有,不如早点散了。”
外婆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眼圈红了。
外公站起身,走到货架前,看着那些绸缎,眼神里满是不舍。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一匹红色的绸缎,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匹,说是杭州最好的织工织出来的。
“这些料子,都是好东西啊。” 他喃喃地说,“可惜了。”
老周叔也走到货架前,看着那些熟悉的布料,叹了口气:“想当年,这些料子刚到的时候,街坊邻里都来抢,生意好得挤都挤不下。”
“是啊。” 外公回过头,看着老周叔,“老周,对不起。跟着我二十年,最后却让你失业了。”
“东家,别这么说。” 老周叔摆了摆手,“能跟着你二十年,我心里踏实。这绸缎庄倒了,可我们的情分还在。”
外公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老周叔:“这里面是你的工钱,还有三个月的遣散费。虽然不多,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周叔接过信封,捏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他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一沓纸币。“东家,太多了。这几个月生意不好,你也不容易,我不能要这么多。”
“拿着。” 外公按住他的手,“这是你应得的。跟着我这么多年,你没少受累。”
老周叔看着外公,眼圈红了。他把信封揣进怀里,然后转身,走到八仙桌旁,拿起那支旧算盘。
那支紫檀木的算盘,跟着老周叔二十年,跟着绸缎庄二十年。算珠被磨得发亮,框子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那是当年绸缎庄遭贼时,被碰倒在地上弄的。
老周叔拿着算盘,走到外公面前,双手递了过去。“东家,这算盘,我用了二十年,现在还给你。”
外公看着那支算盘,愣住了。他伸出手,接过算盘,手指抚摸着光滑的算珠,又摸了摸磨损的框子。
“老周,这算盘是你的,你带着。” 外公的声音有点哽咽,“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做账房,都能用得上。”
“不了。” 老周叔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憨厚的笑,“我年纪大了,不想再做账房了。以后就在家种种地,陪陪孩子。这算盘,是瑞昌祥的东西,应该留在这儿。”
外公拿着算盘,手微微颤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算盘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我看到外公的眼眶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
“老周,你。” 外公的声音很低,却很有力。
“东家,该说的是我。” 老周叔拱了拱手,“二十年的知遇之恩,我记在心里。以后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东家尽管开口。”
外婆走到老周叔身边,递给他一个布包:“这里面是我做的几双布鞋,你拿着穿。家里的孩子也能穿。”
老周叔接过布包,连声道谢:“老板娘,太你了。你做的鞋,又舒服又耐穿。”
老周叔转身,看了看绸缎庄,看了看货架上的绸缎,看了看八仙桌,看了看那扇朱红色的木门。他的眼神里,满是不舍。
“东家,老板娘,我走了。” 他拱了拱手,慢慢向门口走去。
外公拿着算盘,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我看到外公的肩膀微微耸动,泪水终于掉了下来,砸在算盘上,发出轻轻的声响。
老周叔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回过头,又看了一眼绸缎庄,然后推开木门,走了出去。铜环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绸缎庄里,只剩下我、外公和外婆。阳光照进来,落在空荡荡的货架上,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外公手里的算盘上。
外婆轻轻拍着外公的背,轻声说:“别难过了,老周是个厚道人,以后还能再见面。”
外公点了点头,把算盘放在八仙桌上,然后走到货架前,开始整理那些绸缎。他的动作很慢,很轻柔,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这些料子,得找个好归宿。” 外公说,“不能让它们蒙尘。”
接下来的日子,外公开始处理绸缎庄的存货。他把绸缎分成几等,上等的料子,卖给那些还有购买力的人家;中等的,卖给裁缝铺;下等的,就便宜处理给街坊邻里做衣裳。
我和外婆也帮忙,把绸缎打包、称重、算账。没有了老周叔的算盘声,绸缎庄里显得格外安静。外公有时会自己拨拨那支旧算盘,珠子的声响,比以前沉闷了许多。
来买绸缎的人,看到绸缎庄要关门,都叹了口气。张太太也来了,买了一匹黑色的绸缎,说是给她老伴做寿衣。
“瑞昌祥要关门了,真是可惜。” 张太太说,“以后想买这么好的绸缎,都没地方去了。”
“是啊。” 外公笑着说,“以后您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从杭州进货。”
“好,好。” 张太太点了点头,“我信得过你。”
处理完存货,外公把绸缎庄的门脸租了出去,租给了一个开杂货铺的人家。交钥匙那天,外公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朱红色的木门,铜环依旧锃亮,可里面的一切,都变了。
“以后,这里就不是瑞昌祥了。” 外公轻声说。
“可瑞昌祥在你心里,永远都在。” 外婆说。
外公点了点头,牵着我的手,转身离开了。巷口的梧桐,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晃。
回到家,外公把那支旧算盘,放在了堂屋的八仙桌上。他每天都会擦拭一遍,把算珠拨得噼啪响,像是在回忆以前的日子。
过年的时候,老周叔来了。他穿着一件新棉袄,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自家种的红薯和芋头。
“东家,老板娘,给你们拜年了。” 老周叔笑着走进来,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
外公和外婆都很高兴,连忙让他坐下,倒茶递烟。
“家里还好吗?” 外公问。
“挺好的。” 老周叔说,“种了几亩地,收了不少粮食。孩子们也听话,在家帮着干活。”
“那就好。” 外公点了点头,指了指桌上的算盘,“你看,你的算盘,我还留着。”
老周叔看了看算盘,笑了:“这算盘跟着东家,比跟着我好。”
那天,老周叔在我家吃了午饭。外公陪他喝酒,两人聊了很多,聊以前绸缎庄的日子,聊街坊邻里的近况,聊时局的变化。他们的声音不高,却很投机,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临走时,老周叔说:“东家,开春后,我想做点小生意,卖点针头线脑,您觉得怎么样?”
“好啊。” 外公说,“做点小生意,安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东家。” 老周叔拱了拱手,转身走了。
开春后,老周叔的小铺子开起来了,就在巷口的拐角处。铺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还是那么憨厚,对人热情,生意做得不错。
我常常会去他的铺子里玩,他总会给我几颗糖吃。有时,外公也会去,两人坐在铺子里,聊聊天,喝喝茶。老周叔会问起外公的近况,外公会问起他的生意,就像以前在绸缎庄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时局慢慢稳定下来。外公没有再开绸缎庄,而是在家种种花,养养鸟,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外婆依旧操持家务,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渐渐长大,上学、工作、成家。每次回家,都会看到堂屋八仙桌上的那支旧算盘。它依旧被擦拭得锃亮,算珠圆润光滑,框子上的划痕,依旧清晰可见。
外公年纪大了,视力不好,却还是会时不时地拨拨算盘,珠子噼啪响,声音依旧清脆。他说,听到这声音,就想起以前在绸缎庄的日子,想起老周叔,心里就踏实。
老周叔也老了,头发白了不少,背也有点驼了。他的小铺子,交给了儿子打理,自己在家安享晚年。逢年过节,他都会来我家看看外公和外婆,两人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聊着天,脸上满是满足的笑容。
有一年秋天,外公生病了,躺在床上,精神不太好。老周叔听说后,天天都来探望。他坐在外公的床边,握着外公的手,聊着以前的往事,聊着绸缎庄的算盘声,聊着巷口的梧桐。
外公的精神,慢慢好了起来。他说,有老周叔这个老朋友在,他心里高兴。
又过了几年,外公走了。走的那天,很安详。老周叔来送他,哭得像个孩子。他摸着堂屋八仙桌上的旧算盘,哽咽着说:“东家,你走了,我以后跟谁聊天去啊。”
外婆把那支旧算盘,交给了我。她说:“这算盘,是你外公和老周叔的情谊,你要好好保管。”
我接过算盘,感觉沉甸甸的。它不仅是一支算盘,更是一段岁月的见证,一份人情的沉淀。
现在,我也老了。那支旧算盘,依旧摆在我家的堂屋八仙桌上。我常常会给我的孩子们讲起外公的绸缎庄,讲起老周叔,讲起那支旧算盘的故事。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懂民国三十五年的时局,不懂绸缎庄的兴衰,却懂那份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那份藏在算盘珠子里的温暖。
巷口的梧桐,又发新芽了,绿得嫩生生的,风一吹就晃悠。就像民国三十五年的春末,我蹲在绸缎庄的门槛上,听着老周叔拨算盘的声响,那声音,脆生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支旧算盘至今还摆在我家的八仙桌上,珠子的纹路里,藏着一辈子也说不完的人情世故。
注册公司可以为您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合作伙伴。明白了遣散费做账的一些关键内容,希望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丝便捷,倘若你要认识和深入了解其他内容,可以点击主页的其他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