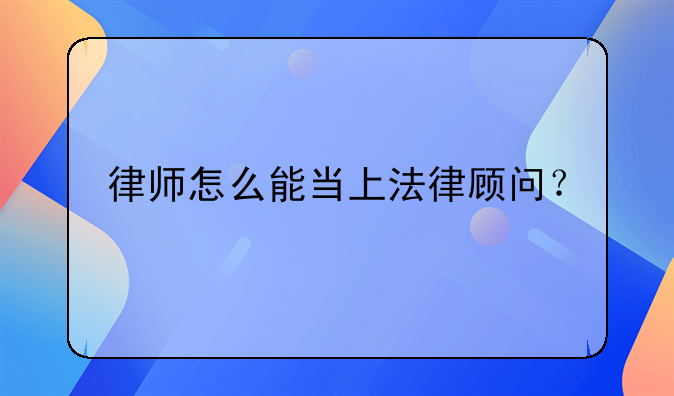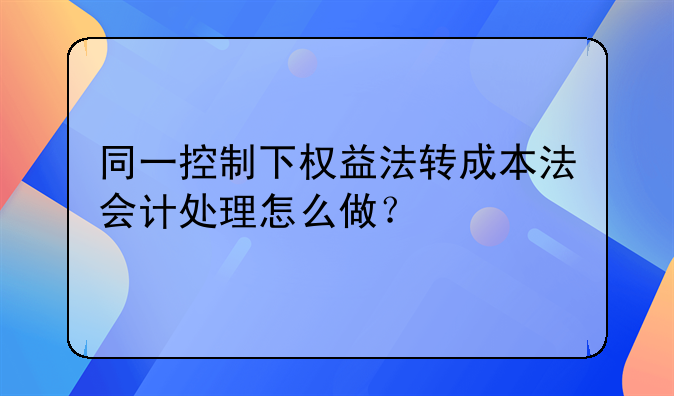咨询电话: 1317-2164-214
男子故意花10万买宝马抵押车后,直奔西藏清欠队跟去僵住:这咋清
发布于 2025-11-28 00:06:05 作者: 业水荷
注册公司是创业者成为合法企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通过完成这个过程,你可以获得法律保护,让你的企业更加正式和专业。主页带大家认识购买车怎么做账,希望看完本文,你会对这方面的认识能更上一层楼。

“十万块钱,买个清净,值。”我对媳妇林玥说这话的时候,正拿抹布擦着手上的机油。
我们家那个小汽修铺,就开在城西老小区的底商,生意不好不坏,养家糊口,绰绰有余。
林玥正拿个小本本记账,闻言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多少波澜,就是那种“你又准备给你弟收拾烂摊子了”的表情。
“梁子,这回又是什么事儿?那辆宝马?”她问。
我点点头,把抹布扔进水桶里,“嗯,就是那辆。我弟梁涛,做生意赔了,把车抵押给一个小贷公司,拿了八万。现在利滚利,滚到十二万了。人家催得紧,说再不还钱,就走程序把车收了。”
“他自己没钱还?”
“他要是有钱,还能叫我么。”我叹了口气。
这事儿说起来也简单。我这个弟弟,梁涛,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主。脑子活,但总用不到正地方。前几年看人家做工程挣钱,自己也跟着掺和,开了个小公司。为了撑场面,贷款买了辆二手的宝马5系。
车是撑场面了,生意没撑起来。最后,连车都给抵了出去。
“那家小贷公司我托人打听了,不是什么正经地方。车要是真被他们收回去,指不定后面还有什么麻烦。”我继续解释,“我找中间人问了,他们也嫌麻烦,说要是有人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十万块钱,车开走,债也清了。”
林玥放下笔,走到我跟前,帮我理了理有点乱的衣领。
“梁子,我知道你心疼你弟。可这事儿,十万块钱买辆抵押车,车还不在咱们手上,这不就是往水里扔钱吗?”
“车在。”我说,“车还在我弟那儿开着呢。那帮人也精,车上装了定位,他们不急着收车,就想让利息多滚几天。我弟现在是开着车也不敢跑远,就在市区里转悠,跟个活靶子似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花十万把车买过来,然后呢?这车又不能过户,就是个铁疙瘩。”林玥的担心很实在。
“我就是买这个铁疙瘩。”我的计划其实很简单,“我花十万,把债权从那家公司手里买过来。车,就归我处置了。他们拿了钱,就不会再找梁涛麻烦。至于这辆车,我开走,开到一个他们找不到,或者说,找到了也无可奈何的地方。”
“什么地方?”
“西藏。”
林玥愣住了,半天没说话。
我知道这个想法听起来有点离谱。一个开汽修铺的,为了弟弟的债务,花十万块钱买个不能过户的抵押车,然后开到几千公里外的西藏去。
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一劳永逸的办法。
梁涛的毛病我知道,耳根子软,还好面子。这次我帮他还了钱,他感激两天,过不了半年,保不齐又被哪个“朋友”忽悠着干点什么事。
我得让他疼一次,让他知道,犯了错,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十万块钱,我不打算白出。我要让他给我写欠条,让他知道,这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他亲哥从牙缝里省出来,帮他填的坑。
而那辆他视若珍宝的宝马车,我要让它从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
“你这是……图啥呢?”林玥最后还是问了。
“图个清净。”我重复了一遍开头的话,“也图让他长点记性。”
林玥没再反对。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她了解我。我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只是默默地回屋,开始给我收拾行李。
我知道,她这是同意了。
事情办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中间人是个姓赵的,人称老赵,专门做这种“不良资产”的撮合生意。我把十万块现金放在他办公室的茶几上,他一张一张地点过,然后把一沓厚厚的合同推到我面前。
“梁老板,敞亮。”老赵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这是原车主,也就是你弟弟,签的抵押合同,这是债权转让协议。你签个字,这车,连同它身上的麻烦,就都是你的了。”
我拿过笔,一页一页地看。合同写得很明白,都是套路,但字字诛心。
签完字,老赵递给我一把车钥匙。
“车钥匙你拿着。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车上有GPS,不止一个。对方公司的人,随时都能看到车在哪儿。”他指了指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喏,就跟这个似的,实时定位。”
“我知道。”
“他们的人,我们行话叫‘清欠队’,专业得很。你把车开走,他们肯定会跟上。到时候怎么处理,就看你的本事了。”老赵说得很轻松,仿佛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趣事。
“他们会动手吗?”我问。
老赵摇了摇头,“那倒不至于。现在都讲文明。他们会跟着你,跟你耗。耗到你受不了,自己把车交出来。或者,找机会用备用钥匙把车开走。这辆车,他们手里应该还有一把钥匙。”
我心里有数了。
从老赵那里出来,我直接去了梁涛家。
他正在家里打游戏,看见我进来,有点不自在地把手柄放下。
“哥,你来了。”
“嗯。”我把车钥匙扔在茶几上,“事情我给你办了。十万块,两清了。这是欠条,你签个字。”
梁涛看着欠条上的“拾万元整”,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拿起笔签了字。
“哥,。这钱,我一定尽快还你。”
“还不还的,以后再说。”我看着他,“车,我得开走。”
梁涛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哥,车你开走干嘛?那是我……”
“是什么?是你撑场面的工具?”我打断他,“梁涛,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意黄了,欠一屁股债,还守着这个空壳子有意思吗?你开着它出去,心里不发慌吗?不怕人家随时把你从车上拽下来?”
他低下了头,不说话了。
“这车,从今天起,跟你没关系了。你给我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把日子过安稳了。什么时候你真正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了,再来跟我谈别的。”
说完,我拿起那把属于宝马车的钥匙,转身就走。
我知道他会不理解,甚至会有点怨我。
但长痛不如短痛。
下楼,我看到了那辆灰色的宝马5系。车身洗得挺干净,看得出梁涛平时很爱惜。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里还有他常用的那款古龙水味道。
我发动车子,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开向了城外的高速入口。
我知道,从我发动车子的那一刻起,那个所谓的“清欠队”,就已经在屏幕后面,看到我了。
他们的游戏,开始了。我的游戏,也开始了。
第一天,风平浪静。
我沿着高速一路向西,开得不快不慢。我猜,他们可能觉得我只是在郊区兜风,或者想找个地方把车藏起来。
我没有做任何反侦察的动作,比如拆GPS或者进信号屏蔽区。
我要的就是让他们跟着。
晚上,我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找了家旅馆住下。车就停在旅馆门口的停车场,大大方方的,生怕别人看不见。
我一夜睡得很好。
第二天,我继续上路。路线很明确,G318国道,川藏线的方向。
开到下午,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一辆黑色的帕萨特。
它不远不近地跟着我,车速和我保持一致。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
我知道,是他们来了。
我没慌,甚至还有点想笑。这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玩的警察抓小偷的游戏。
我在前面的服务区停了车,下去买了瓶水,还顺便加了油。
那辆帕萨特也停在了不远处,车上下来两个男人,都穿着黑色的夹克,平头,看着挺精神。他们没看我,也没靠近我的车,只是点了根烟,靠在车边抽。
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余光一直在我身上。
我加完油,回到车上,继续出发。
他们也掐了烟,上车,跟了上来。
这种猫鼠游戏,一直持续到傍晚。
我把车开进雅安市区,找了个热闹的夜市,把车停在路边,自己找了个小摊吃晚饭。
那辆帕萨特就停在斜对面的街角。车里的人没下来。
我一边吃着串串,一边观察他们。
这就是老赵说的“耗”。他们有耐心,也有时间。他们就像是狼,盯着自己的猎物,等待猎物露出疲态,或者犯下错误。
可惜,我不是一般的猎物。
吃完饭,我溜达着回了停车的地方。
走到车边,我看到一个男人正靠在我的车门上。就是白天在服务区看到的其中一个。
他看到我,站直了身子,脸上没什么表情。
“先生,你好。”他开口了,声音很平静。
“你好。”我也很平静。
“这辆车,有点问题。跟我们走一趟吧。”他说。
“什么问题?”我明知故问。
“车主有笔账没结清,我们是来处理这笔账的。”他说话很客气,但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哦,你们说的是梁涛吧?”我笑了笑,“他的账,我已经结清了。这车,现在是我的。”
男人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他大概是头一次遇到我这种“接盘侠”。
“你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有手续吗?”
“有。”我从包里拿出那份债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递给他,“喏,白纸黑字,看清楚了。我现在是这辆车的债权人。从法律上讲,这车归我处置。”
男人接过协议,凑着路灯仔细看了看。他旁边,另一个男人也走了过来。
他们俩研究了半天,又交头接耳了几句。
最后,那个男人把协议还给我,脸上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像是意外,又像是觉得棘手。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他说,“这车你又不能过户,买来干嘛?”
“我乐意。”我收回协议,拉开车门,“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没再理他们,发动车子,汇入了车流。
后视镜里,他们俩站在原地,看着我的车尾灯,没有立刻跟上来。
我知道,我的第一步棋,走对了。
我把事情从一个简单的“收车”,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债权纠纷”。
他们是来找梁涛的麻烦的,但我现在成了新的债权人。他们再想用以前那套对付梁涛的办法来对付我,就行不通了。
至少,不能那么理直气壮了。
但我也知道,这事儿没这么容易结束。
他们只是暂时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果然,半小时后,那辆黑色的帕萨特,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后视镜里。
这一次,他们跟得更紧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进入了真正的拉锯战。
我翻越二郎山,穿过康定城,海拔越来越高,路也越来越险。
我的那辆二手宝马,性能还算不错,应付这种路况,不算吃力。
但帕萨特就有点勉强了。好几次,我都能从后视镜里看到它在盘山路上挣扎的样子。
可他们就是不放弃。
我白天开车,他们就跟着。我晚上住店,他们就在附近找地方住下。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
路上遇到,我们会点点头,像老熟人一样。在饭店吃饭,如果碰到了,他们会坐到离我最远的一张桌子。
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但谁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和目的。
有一次,在理塘,世界高城。我有点高原反应,头疼得厉害,就在酒店里多休息了一天。
那天下午,我正在房间里喝着酥油茶,房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是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年纪稍长一些的那个。
他手里提着一个果篮。
“你好,梁先生。”他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我叫强子。看你今天没出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们老板让我来看看你。”
我有些意外。
“你们老板?”
“对,我们也是给人打工的。”强子说,“我们老板姓王,他说,跟你也算不打不相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我让他进了屋。
他把果篮放下,很自来熟地坐到沙发上。
“梁先生,你这又是何苦呢?”强子给我递了根烟,我摆手拒绝了。
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我们查过了,你跟你弟弟梁涛的关系。我们知道,你是好心,想帮他。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哦?那你说,怎么才能解决问题?”我问。
“很简单。你把车给我们。我们拿到车,回去跟公司交差。至于你和你弟弟之间的事,那是你们的家事,我们不管。你花的十万块钱,就当是替你弟弟交了个学费。”强子的语气很诚恳。
“学费?”我笑了,“这学费有点贵。而且,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
强子叹了口气,“梁先生,我们是正规公司,不是你想的那种。我们有专业的法务团队。你手里的那份协议,我们研究过了,是有法律效力的。但是,这辆车的第一债权人,是我们公司,因为原车主,也就是你弟弟,是先把车抵押给我们的。你的债权,是次级债权。真要打起官司来,你赢不了。”
“我知道。”我说,“我没打算跟你们打官司。”
“那你图什么呢?把车开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就为了跟我们耗着?”强子有点不解。
“我说了,图个清净。”
强子看着我,沉默了。
他抽完一支烟,站起身,“行吧。话我带到了。我们老板的意思是,和气生财。希望你再考虑考虑。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陪你慢慢玩。”
说完,他走了。
看着桌上的果篮,我心里很清楚。
这是先礼后兵。
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了。从一开始的强硬对峙,变成了现在的怀柔劝说。
这说明,我的坚持,让他们感到了麻烦。
西藏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他们在这里,很多手段都施展不开。在这里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
他们也怕麻烦。
这更坚定了我继续下去的决心。
过了理塘,路况变得更差,天气也愈发多变。
有一天,下起了大雪。
鹅毛般的大雪很快就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毯。路面结冰,非常湿滑。
我的车是后驱,在这种路面上,简直就是个灾难。
在一个拐弯处,我操作稍有不慎,车子侧滑,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好在车速不快,人没事,但车头被撞得变了形,水箱也漏了。
车,趴窝了。
我坐在车里,看着前方案件的白雪,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动摇。
我这是在干什么?
一个人,开着一辆不属于自己的车,在几千公里外的高原上,跟一群陌生人较劲。
家里,林玥和孩子肯定在担心我。我的汽修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就在我发呆的时候,那辆黑色的帕萨特,缓缓地停在了我的车后。
强子和他那个同伴下了车,朝我走来。
我以为他们会幸灾乐祸,或者趁机逼我交出车钥匙。
但没有。
强子走到我车窗前,敲了敲玻璃。
我摇下车窗。
“梁先生,人没事吧?”他问。
“没事。”
“车坏了?”
“嗯,水箱破了。”
他和他同伴绕着车看了一圈,然后回来说:“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也没信号。你等在这儿不是办法。这样,你上我们车,我们送你到前面的县城。你的车,我们帮你看着。”
我看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
但他表情很真诚,不像是在演戏。
“你们……帮我?”
“出门在外,互相搭把手,应该的。”强-子说,“我们跟你,是工作。但做人,是另一码事。”
我沉默了。
说实话,我很意外。
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应该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但现在,他们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援手。
我最终还是上了他们的车。
车里暖气开得很足。强子的同伴,那个一直不怎么说话的年轻人,递给我一瓶热水。
“喝点吧,暖暖身子。”
“。”
车子在冰雪路面上缓慢行驶。
“梁先生,你是个体面人。”强子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们老板很欣赏你。他说,能想出这种办法,还真能一个人开车跑到这里的人,不是一般人。”
“我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可干不出这事。”强子笑了笑,“说实话,我们干这行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哭的,闹的,耍赖的,玩消失的。像你这样的,头一个。”
“所以呢?”
“所以,我们老板想跟你当面谈谈。”强子说,“他今天晚上会到巴塘县。他想请你吃个饭。”
我明白了。
车祸是意外,但这个饭局,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
他们真正的老板,要出面了。
这盘棋,要进入中局了。
“好。”我答应了。
我知道,我没有拒绝的余地。
而且,我也想见见这个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王老板”。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巴塘县城不大,但很热闹。
强子把我带到一家看起来很不错的川菜馆。
包间里,一个中年男人已经坐在那里喝茶了。
他大概四十多岁,微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色的休闲夹克。看起来不像个放贷公司的老板,倒像个大学老师。
“梁先生,你好。我是王海。”他站起来,主动跟我握手。
他的手很温暖,也很有力。
“王老板。”
“别客气,坐。”王海招呼我坐下,亲自给我倒了杯茶,“强子他们,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没有,他们很‘照顾’我。”我意有所指地说。
王海笑了,“他们是干这个的,职责所在。不过,我对他们有要求,绝对不能用暴力,不能违法。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正经生意人,会放利滚利的贷?”我问。
王海的笑容不变,“梁先生,存在即合理。你弟弟梁涛,当初缺钱的时候,银行会贷款给他吗?不会。只有我们这种公司,愿意承担风险,把钱借给他。我们承担了风险,自然要追求高回报。这是市场规律。”
我无话可说。
他说的,是歪理,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却又真实得让人无法反驳。
“梁先生,我们明人不说暗话。”王海把茶杯放下,看着我,“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重情义的人。你为了你弟弟,花了十万块,跑了几千公里,跟我们耗了这么多天。这份情义,我佩服。”
“但是。”他话锋一转,“你这样做,没有意义。你既保不住车,也解决不了你弟弟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我弟弟的根本问题?”
“他的根本问题,是认知和能力,配不上他的欲望。”王海一针见血,“他想当老板,想开豪车,想过人上人的生活。但他没有与之匹配的商业头脑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他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再次沉默了。
这个王老板,看人看事,确实很透彻。
“你这次帮他把车‘保’下来了,他会感激你。但是,他会觉得,天塌下来,有你这个哥哥顶着。他不会真正反思自己的问题。下一次,他可能会捅出更大的娄子。到那时候,你还能帮他扛吗?”
王海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我这次的行为,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
我以为我是在让他“长记性”,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又何尝不是在给他提供一个“犯了错也没关系,反正有我哥”的心理依赖?
我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那王老板觉得,我该怎么做?”我问。
“很简单。”王-海说,“把这件事,交还给你弟弟自己处理。”
“他处理不了。”
“不试试怎么知道?”王海笑了,“梁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你对你弟弟的保护,可能太周到了?你就像一个园丁,总怕小树被风雨吹倒,给它搭上支架,遮风挡雨。结果,这棵小树,永远也长不成参天大树,因为它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雨,根扎得不够深。”
“你让他自己来面对我们。让他自己来跟我谈,这笔账,到底该怎么还。让他自己来承担,他犯错的后果。”
“他要是来了,你们会怎么对他?”
“我们不会怎么对他。我们只会跟他谈钱。”王海说,“车,我们肯定要收回。这是原则。至于剩下的两万块钱,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分期,让他慢慢还。利息我们也可以减免一部分。我们求的是财,不是为了把人逼上绝路。”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今天坐在这里,心平气和地跟你谈。而不是让强子他们,用别的办法把车抢走。”王-海看着我,眼神很真诚,“梁先生,我们虽然是债主,但也讲道理。你是个讲道理的人,所以,我才愿意跟你讲道理。”
那顿饭,我吃得五味杂陈。
王海没有再逼我,他只是跟我聊了很多。聊他的创业史,聊他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聊他对人性的看法。
他是个很健谈,也很有思想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对立,我甚至觉得,可以跟他交个朋友。
吃完饭,他让强子送我回酒店。
临走前,他对我说:“梁先生,你好好想想。想通了,给我打电话。你的车,我已经让强子联系了修理厂,明天他们会派拖车过去。修车的钱,算我的。”
回到酒店,我一夜没睡。
王海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一个一直不愿去触碰的盒子。
这些年,我为梁涛收拾了多少烂摊子?
他上学时跟人打架,我去学校给他道歉。
他工作后嫌工资低,三天两头换工作,我托关系给他找门路。
他要创业,钱不够,我把准备给儿子上兴趣班的钱拿给了他。
每一次,我都以为自己是在帮他。
但结果呢?
他变得越来越依赖我,越来越没有担当。
就像王海说的,我一直在给他搭支架,却忘了,他需要自己去扎根。
我这次千里迢迢来西藏,自以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既能保住财产,又能给他一个教训。
可现在看来,我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错在,又一次把他挡在了我的身后。
我剥夺了他亲自面对错误,承担后果的机会。
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和远处连绵的雪山轮廓,心里一片茫然。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清醒的,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
可到头来,我可能才是那个问题本身。
我拿出手机,翻到了梁涛的电话。
我想打给他,想把他骂一顿,想质问他为什么总是这么不争气。
但最终,我还是把手机放下了。
骂他,有用吗?
没有用。
我需要想明白的,是我自己。
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弟弟?
是一个永远需要我保护的,长不大的孩子?
还是一个能够独立行走,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
答案不言而喻。
第二天一早,修理厂的拖车来了。
强子也在。他监督着工人把宝马车小心地拖上板车,然后过来跟我说:“梁先生,车我们先拉去修。王总的意思是,不管你最后怎么决定,车,都得先修好。”
我点了点头,“替我王总。”
“客气了。”
看着宝马车被拖走,我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轻松。
这个我一路开过来,小心守护的“烫手山芋”,暂时离开了我。
我也终于可以从这场猫鼠游戏中,暂时抽身出来,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在巴塘又待了两天。
这两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县城里闲逛。
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藏族同胞,看着他们脸上那种被高原阳光雕刻出来的,平静而坚毅的表情。
我看着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白云下,显得那么圣洁和永恒。
在这里,时间仿佛都变慢了。
我的心,也慢慢地静了下来。
我想了很多。想起了我和梁涛小时候的事。
那时候,我是哥哥,他是弟弟。有好吃的,我总是先让他吃。被人欺负了,我总是第一个冲上去。
这种“保护者”的角色,我当了三十年。
已经成了一种本能。
可是,我们都长大了。
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把他护在身后。
我必须学会放手。
哪怕这个过程会让他很痛,也必须让他自己去经历。
想通了这一点,我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给王海打了电话。
“王总,我想通了。”
“我就知道,梁先生是个明白人。”电话那头,王海的声音带着笑意。
“车,我不要了。”我说,“你们拿走吧。至于我花的那十万块钱,就当我替我弟还了一部分。剩下的,你们跟他谈。”
“好。”王海很干脆,“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建议。你应该让你弟弟,亲自来一趟。”
“为什么?”
“因为,只有让他亲自站在这里,看着他为了虚荣买来的车,被我们开走,他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失去’。只有让他亲自面对我们,为剩下的债务签字画押,他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责任’。这个教训,比你说一万句,都管用。”
我沉默了。
王海说得对。
这个仪式感,很重要。
“好。”我说,“我让他来。”
挂了电话,我拨通了梁涛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他才接。
“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和心虚。
“梁涛,你现在立刻买票,来西藏巴塘。”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决。
“去……去西藏干嘛?”他显然很意外。
“来处理你自己的事。”我说,“你的车,在这里。追债的人,也在这里。他们老板要见你,亲自跟你谈剩下的账怎么还。”
电话那头,梁涛沉默了。
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慌乱和恐惧。
“哥,我……我不敢去。你帮我处理了吧。我以后一定好好挣钱还你。”他开始退缩了。
“梁涛,我问你,你是不是个男人?”我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
“是男人,就自己过来,把你自己的烂摊子收拾干净!我不可能护你一辈子!这次,你必须自己面对!”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你要是不来,从今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你自己看着办。”
说完,我挂了电话。
我知道,我的话很重。
可能会伤到他。
但良药苦口。
有些事,必须下狠心。
我不知道梁涛会不会来。
我在赌。
赌他心里,还存留着一丝作为男人的血性和担当。
接下来的两天,是漫长的等待。
我没有再联系梁涛,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强子他们也没有再来找我。整个县城,安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心里没底。
如果梁涛真的不来,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要跟他断绝关系吗?
我做不到。
他是我的亲弟弟。
就在我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接起来。
“哥,我到了。”
是梁涛的声音。
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来了。
他终究还是来了。
我在汽车站接到了他。
他穿着一件单薄的夹克,背着一个双肩包,嘴唇因为高原反应而有些发紫。整个人看起来又瘦又憔悴。
看到我,他低下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哥。”
我没说话,走过去,接过他的包,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先去吃饭。”
我带他去了王海请我吃饭的那家川菜馆。
我给他点了他最爱吃的回锅肉和麻婆豆腐。
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像是饿了很久。
吃着吃着,他的眼圈红了。
“哥,对不起。”他放下筷子,声音哽咽。
“吃饭。”我给他夹了一筷子菜,“吃完了,才有力气去解决问题。”
他点了点头,埋头继续吃。
那顿饭,我们兄弟俩,谁都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第二天,我带着梁涛,去见了王海。
见面的地点,在修理厂。
那辆灰色的宝马车,已经被修好了,停在院子里,洗得干干净净,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梁涛看着那辆车,眼神很复杂。有不舍,有悔恨,也有解脱。
王海还是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他没有为难梁涛,只是把一份新的还款协议,放在他面前。
“梁涛,是吧?”王海说,“你哥,已经替你还了十万。剩下的两万,我给你免了利息,分十二期,每个月还一千六百多。你有没有问题?”
梁涛看了看我。
我对他点了点头。
他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车,我们开走了。”王海收起协议,对强子使了个眼色。
强子拿着钥匙,走向那辆宝马车。
车子发动,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
梁涛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宝马车缓缓地驶出修理厂的大门,汇入了车流,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
一切都结束了。
“你有个好哥哥。”王海走到梁涛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好自为之。”
说完,他也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兄弟俩。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哥,我们……回家吧。”梁涛轻声说。
“嗯,回家。”
回去的路上,我们坐的是长途大巴。
车子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窗外是壮丽的雪山和辽阔的草原。
梁涛一直看着窗外,没怎么说话。
我知道,这次西藏之行,对他来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他失去了一辆车,但找回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比如,责任和担当。
快到家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哥,我回去以后,不打算再自己干了。我想去你店里帮忙,从学徒干起。你收我吗?”
我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没有了以前的浮躁和好高骛远,多了一份踏实和坚定。
我笑了。
“好啊。”我说,“不过,我可不给你发高工资。”
“没事,管饭就行。”他也笑了。
那是他来到西藏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
回到家,林玥已经做好了饭菜。
看到我们俩平安回来,她什么也没问,只是一个劲地往我们碗里夹菜。
吃完饭,我把梁涛签的那张十万块的欠条,拿了出来。
当着梁涛和林玥的面,我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了。
火苗升起,很快就把那张纸,烧成了灰烬。
“哥,你这是……”梁涛不解地看着我。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说,“从今天起,你不是欠我钱,而是欠你自己一个未来。好好干,别让我失望。”
梁涛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他没有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懂了。
后来,梁涛真的来我的汽修铺上班了。
他脱下了名牌衣服,换上了沾满油污的工作服。
从最基础的换轮胎、做保养开始,一点一点地学。
他干活很卖力,也很用心。手上的老茧,一天比一天厚。脸上的笑容,也一天比一天真实。
店里的老师傅都夸他,说这小子,是块好料。
一年后,他用自己攒下的工资,还清了王海公司的最后一笔欠款。
那天,他拿着还款凭证给我看,笑得像个孩子。
我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有时候,林玥会跟我开玩笑,说我那十万块钱,花得真值。
不仅买了个清净,还“买”回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弟弟。
我每次都只是笑笑。
我知道,改变梁涛的,不是我,也不是那十万块钱。
是那段几千公里的旅程,是高原上凛冽的风,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是那辆最终失去的宝马车。
更是他自己,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内心深处真正的觉醒。
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哥哥,应该做的事。
我学会了放手。
而他,学会了成长。
这可能,才是我们家这几年里,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从上文内容中,大家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购买车怎么做账的信息。了解完这些知识和信息,主页希望你能更进一步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