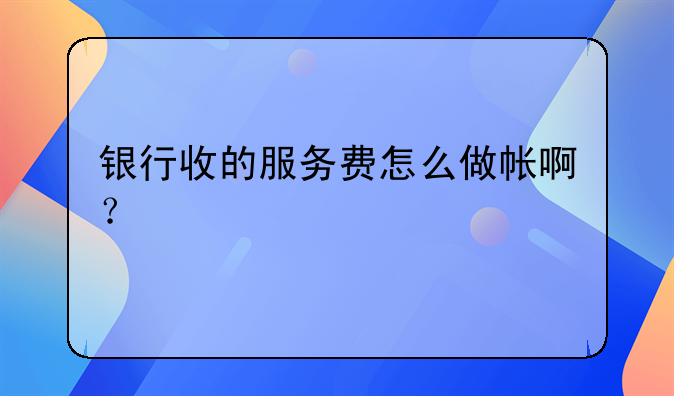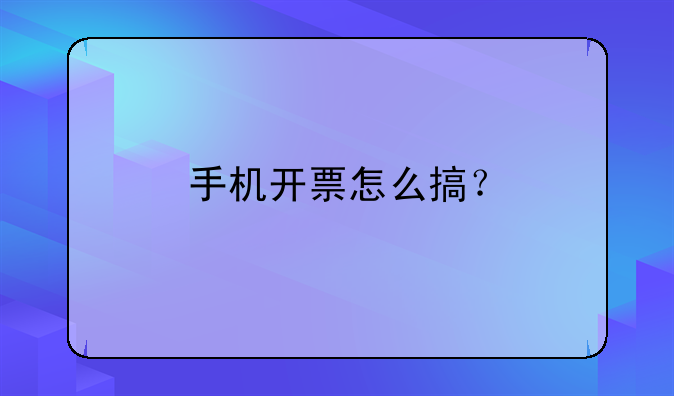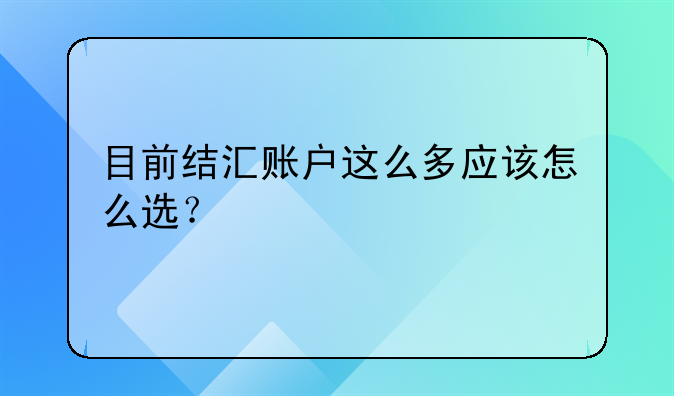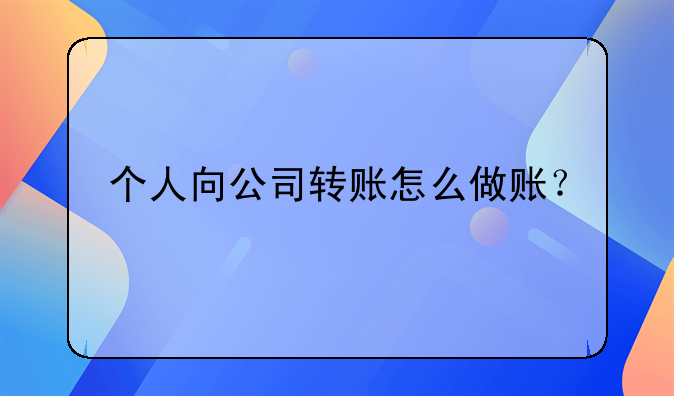咨询电话: 1317-2164-214
退休丈夫坚持AA,他生病住院让我陪护,我:按小时收费
发布于 2026-01-15 23:18:03 作者: 乘慧雅
注册公司是创业者成为合法企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通过完成这个过程,你可以获得法律保护,让你的企业更加正式和专业。主页将带你了解陪护费怎么做账,希望你可以从中得到收获。

第一章 账本
赵秀兰在灯下,一笔一划地记着账。
这是她自己的账本,一个巴掌大的软皮抄,封皮的红塑料已经卷了边。
她记下:菠菜,两块三。
鸡蛋,六块五。
猪肉,十四块。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塞进电视柜和墙壁的夹缝里。
客厅另一头,她的丈夫张建国,也正低头做着同样的事。
他的账本要气派得多。
硬质的牛皮封面,里面是专门的账本内页,分着“日期”、“摘要”、“收入”、“支出”、“结余”。
张建国扶了扶老花镜,用钢笔清晰地写下:晚餐食材支出,二十二块八,本人承担十一块四。
写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盒子,那是以前装清凉油的。
他数出十一块四毛钱,走到赵秀兰面前,把钱放进她手里。
“今天的菜钱。”
他的语气,像是在完成一项工作交接。
赵秀兰没说话,接过钱,放进自己那个同样藏在夹缝里的饼干盒。
盒子里,是几十年攒下的零零碎碎。
这样的日子,他们过了三十年。
从儿子张伟上小学开始,张建国就郑重地提出了“家庭财务AA制”。
他说,这是新思想,夫妻双方经济独立,人格才独立。
他说,亲兄弟明算账,夫妻之间把账算清楚,才能避免矛盾,感情才能长久。
赵秀兰不懂这些大道理。
她只知道,从那天起,这个家就变成了两半。
买米,一人一半钱。
买菜,称好了算清楚,你今天吃了多少,我明天吃了多少,月底拉个总账。
水电煤气费,账单来了,除以二。
就连儿子张伟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一人一半。
张建国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尤其是在钱上。
他年轻时在单位管过仓库,练就了一身算账的本事。
他觉得这叫“公平”。
赵秀兰觉得,这叫“生分”。
但她嘴笨,吵不过他。
他说一套一套的,什么西方先进家庭模式,什么保持个人边界。
赵秀兰吵急了,只会说一句:“哪有两口子过日子像你这样的?”
张建国就会冷笑一声:“那是他们糊涂,过的是糊涂账,早晚要出问题。”
后来,赵秀兰也就不吵了。
她也学着他,备了一个小账本。
他不让她糊涂,她就算清楚给他看。
只是,他的账本放在书架上,像个光荣的勋章。
她的账本,藏在夹缝里,像个委屈的秘密。
退休后,两个人的退休金也是各管各的。
张建国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很有规划。
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回来自己煮一壶养生茶,看报纸,研究股票。
他的退休金比赵秀兰高一些,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赵秀兰的生活就简单得多。
打扫屋子,买菜做饭,去楼下跟老姐妹们聊聊天。
有时候,她看着张建国在阳台上,悠闲地侍弄他那些花草,会觉得那个人离自己很远。
明明是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却像是合租的室友。
上个星期,赵秀兰的侄女要结婚。
她想包个大点的红包,毕竟是自己娘家最亲的下一代。
她自己的退休金紧巴巴的,就跟张建国商量。
“建国,小萍要结婚了,你看我们包多少合适?”
她特意用了“我们”这个词,带着一丝小小的期盼。
张建国头都没从报纸上抬起来。
“你娘家的亲戚,你自己看着办。”
“我的钱不太够,想……”
“不够就少包点,心意到了就行。”
赵秀兰的脸一下子就热了。
“我是想,你能不能先借我点,我下个月退休金发了就还你。”
张建国这才放下报纸,看着她,眼神里带着点审视。
“借多少?”
“一千。”
“要写借条。”
赵秀兰的心,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
她看着张建国那张无比认真的脸,突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最后,她回自己房间,从箱底翻出一个旧手镯。
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她一直舍不得戴。
她拿去金店卖了,换了两千块钱。
给侄女包了一千八的红包,剩下两百,她揣在兜里,心里空落落的。
从金店回来的路上,她看到路边有一家小小的咖啡馆。
她从来没进去过。
她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点了一杯最便宜的拿铁。
三十八块钱。
她在自己的小账本上,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记下这笔“奢侈”的支出。
就当是……自己偷偷藏起来的一点甜头吧。
喝完咖啡,她把纸杯扔进垃圾桶,好像也把那一瞬间的勇气和叛逆,一起扔掉了。
回到家,张建国依然在看他的报纸。
他问她:“钱的事情解决了?”
赵秀兰“嗯”了一声。
“那就好。”
他又低头看报纸去了,没问她是怎么解决的。
或许在他看来,那是她的事,与他无关。
就像这三十年来,她所有的心事一样。
晚上,赵秀alaram地记下今天的开销。
张建国走过来,放下十一块四毛钱。
灯光下,他花白的头发,和他手里的零钱,都显得那么刺眼。
赵秀兰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
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也就这样了。
守着一个室友,守着一本账,一天天,一年年,直到老去。
第二章 裂缝
变故来得很突然。
那天下午,赵秀兰正在厨房择菜,听见客厅“咚”的一声闷响。
她跑出去一看,张建国倒在沙发边上,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他手里的报纸散落一地。
赵秀alaram坏了,手里的青菜都掉在了地上。
“建国!建国!你怎么了?”
她冲过去扶他,他的身体软得像一摊泥。
张建国嘴唇哆嗦着,想说话,却发不出清晰的声音。
“头……头晕……”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赵秀兰这辈子没经过这种事,一时间手足无措。
她赶紧摸出手机,哆哆嗦嗦地给儿子张伟打电话。
“小伟!你快回来!你爸……你爸晕倒了!”
张伟在电话那头也急了,让她赶紧打120。
挂了电话,赵秀兰又手忙脚乱地拨了急救电话。
等救护车的时候,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赵秀兰半跪在地上,抱着张建国,不停地给他擦汗。
她第一次发现,这个平时在她面前总是一副强者姿态的男人,原来也会这么脆弱。
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眼神里是她从未见过的惊慌和依赖。
救护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
在医院,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检查,医生把赵秀兰和匆匆赶来的张伟叫到办公室。
“是突发性脑梗,幸好送来得及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医生的话让赵秀兰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但是,”医生话锋一转,“病人需要立刻住院治疗,而且后续的康复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他现在半边身子活动不便,需要人二十四小时在旁边照顾。”
二十四小时照顾。
这六个字,像一块石头,砸在了赵秀兰的心上。
张伟一脸凝重,对医生说:“医生,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治疗。”
办完住院手续,张建国被送进了病房。
他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刚才的混乱和惊吓过后,他似乎恢复了一些平日里的冷静,但脸色依然难看。
张伟忙前忙后,买脸盆,买毛巾,买各种住院需要的东西。
赵秀alaram坐在病床边,看着张建国。
她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方面是后怕,怕他就这么倒下去了。
另一方面,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茫然。
照顾他?
怎么照顾?
像以前一样,给他做饭,然后问他收一半的饭钱吗?
给他擦身子,是不是也要算一下用了多少水,多少毛巾?
这些荒唐的念头,不受控制地从她心里冒出来。
张伟买东西回来,看到母亲愣愣地坐着,以为她吓坏了。
“妈,你别担心,医生说爸送来得及时,好好治疗会恢复的。”
赵秀兰点点头,没说话。
张伟又对张建国说:“爸,你安心养病,钱的事你别操心,我这有。”
张建国嘴唇动了动,从生病到现在,他第一次开口说了句完整的话。
“让你妈……去把我的医保卡、银行卡都拿来。”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我的账本,在书桌第二个抽屉里。”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没忘记他的账本。
赵秀兰的心,又凉了半截。
张伟叹了口气,对赵秀兰说:“妈,你先回去拿东西,顺便熬点粥带过来,我在这守着。”
赵秀兰站起身,像个木偶一样,点了点头。
她走出病房,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让她一阵反胃。
回到那个熟悉的家,一切都和她离开时一样。
厨房地上还散落着她掉落的青菜。
客厅里,张建国的报纸也还摊在地上。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赵秀兰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裂开了一道缝。
她走到书桌前,拉开第二个抽屉。
张建国的那个牛皮账本,就静静地躺在里面。
她拿起来,翻开。
里面密密麻麻,记录了三十年的“公平”。
最后一页,是他今天下午刚刚记下的:晚餐食材支出,二十二块八,本人承担十一块四。
字迹刚劲有力,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
他是在记完这笔账之后,倒下的。
赵秀兰的手指抚过那行字,仿佛还能感觉到他落笔时的那种理所当然。
她把账本合上,和银行卡、医保卡一起,放进包里。
她没有去厨房熬粥。
她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很久。
从窗外最后一丝光亮,到整个屋子都陷入黑暗。
她没有开灯。
就在这片黑暗里,一个念头,像一粒被压在石头下很久的种子,终于顶开了石头,带着一种决绝的姿态,破土而出。
第三章 “责任”
赵秀兰再次回到医院时,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但里面不是粥。
是她回家前,在楼下餐馆打包的一份青菜瘦肉粥。
二十块钱。
她把发票小心地叠好,放进了口袋里。
张伟看到她回来,松了口气。
“妈,你可回来了,爸刚还念叨你呢。”
赵秀兰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看了一眼张建国。
张建国也正看着她,眼神复杂。
有病痛带来的脆弱,有对未知的恐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东西都拿来了?”他问,声音有些沙哑。
“嗯。”
赵秀alaram把他的医保卡、银行卡,还有那个牛皮账本,都放在了床头柜上。
张建国看到账本,眼神似乎安定了一些。
“小伟,你明天还要上班,先回去吧。这里有你妈在就行了。”张建国对儿子说。
他说话的语气,自然而然,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
好像赵秀兰在这里照顾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张伟有些犹豫:“妈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我今晚在折叠床上对付一下。”
“不用!”张建国立刻拒绝了,“一个大男人,睡不好明天怎么上班?让你妈在这,她一个退休的,时间多。”
赵秀兰一直没说话,就静静地听着。
她看着张建国那张苍白的脸,和他嘴里说出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话,心里那道裂缝,在一点点扩大。
张伟拗不过父亲,又看母亲没什么异议,只好嘱咐了几句,先离开了。
病房里,一下子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倒杯水。”张建国开口,打破了沉默。
赵秀兰拿起暖水瓶,给他倒了一杯温水,用棉签沾着,一点点喂到他嘴边。
他的嘴唇干裂,喝水的动作很费力。
赵秀兰的动作很轻,很稳。
没有关心,也没有怨恨。
就像一个护工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喝完水,张建国似乎缓过来一些。
“粥呢?熬了没?”
“买了。”赵秀兰打开保温桶,“医生说你现在只能吃流食。”
张建国眉头一皱:“买的?我不是让你熬吗?买的多贵,还不知道干不干净。”
又是钱。
赵秀兰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她没接话,盛了一碗粥,准备喂他。
张建国看着她,忽然又开口了,语气里带着一丝教导的意味。
“秀兰,我知道我这次病得突然,你可能有点慌。”
“但是别怕,钱的事情我自己都算着呢。住院的钱,用我的医保和存款,绝对不会花到你一分钱。”
“你就安安心心照顾我就行了。”
“毕竟,我们是夫妻。我生病了,你照顾我,这是你的责任。”
责任。
这个词,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了赵秀兰的心上。
三十年来,他跟她算清了每一分钱,把家变成了账房。
现在他倒下了,不能自理了,就想起了“夫妻”和“责任”。
原来,在他的账本里,“责任”是单向的。
是她对他应尽的,免费的义务。
赵秀兰端着粥碗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她抬起头,几十年来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平静地直视着张建国的眼睛。
张建国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你看我干什么?喂我啊。”
赵秀兰没有动。
她就那么看着他,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她缓缓地开口了。
她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这间安静的病房。
“张建国。”
她第一次这样连名带姓地叫他。
“照顾你可以。”
张建国的脸上露出一丝“我就知道”的表情。
“但是,”赵秀alaram继续说,“我们得先把账算清楚。”
张建国愣住了。
“算……算什么账?”
赵秀兰把粥碗放在床头柜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买粥的发票,放在他面前。
“青菜瘦肉粥,二十块。这是你吃的,应该你付钱。”
张建国的眼睛猛地睁大了,里面全是难以置信。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秀兰没有理会他的震惊,继续平静地说着,仿佛在谈论今天的天气。
“还有,从我下午接到电话,赶来医院开始,我的时间就不再是我自己的了。”
“我需要在这里二十四小时看着你,喂你吃饭,给你擦身,帮你大小便。”
“这些,都不是免费的。”
她看着他已经开始扭曲的脸,一字一顿地,说出了那句在她心里盘旋了半天的话。
“张建国,我们还是按你的老规矩来。”
“陪护,一小时五十块钱,吃饭喝水另外算。”
“你看,这个价格,公不公平?”
第四章 价目表
病房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被抽干了。
张建国死死地盯着赵秀alaram,那张因脑梗而略显僵硬的脸上,肌肉在不住地抽搐。
他的嘴唇哆嗦着,一半是病理性的,一半是气愤。
“你……你说什么?”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在他面前顺从了三十年的女人,这个他以为只要拿出“责任”二字就能轻松拿捏的妻子,竟然会跟他提钱。
而且,是用他最熟悉的方式——明码标价。
赵秀兰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她甚至从床头柜上拿过纸和笔,那是张伟买来给医生记录病情用的。
她把纸铺在张建国的牛皮账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
“陪护服务价目表。”
“日间陪护(早八点至晚八点):50元/小时。”
“夜间陪护(晚八点至早八点):60元/小时(含起夜、翻身等服务)。”
“餐费:实报实销(凭发票结算)。”
“其他护理服务(如擦身、协助如厕等):每次10元。”
她写得很认真,字迹工整,就像他当年教她记账时一样。
写完,她把那张纸推到张建国面前。
“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我们就从今天下午三点,我接到电话那一刻开始算。”
张建国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监护仪上的心率数字开始不规律地跳动。
“赵秀兰!”
他猛地吼了一声,声音嘶哑而尖利。
“你疯了!我是你男人!你跟我算这个账?”
他想挣扎着坐起来,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只是徒劳地在床上扭动着,样子狼狈不堪。
“你没疯,我也没疯。”赵秀alaram说,“我只是在用你教我的方法做事。”
“你不是说,亲兄弟明算账吗?”
“你不是说,把账算清楚,关系才能长久吗?”
“三十年了,我一直在学,今天,总算是学出师了。”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精准地戳在张建国最在意、也最引以为傲的那些“原则”上。
张建国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的手都在抖。
“你……你这是趁火打劫!你这是不仁不义!”
“仁义?”赵秀alaram轻轻地笑了,那笑声里带着无尽的悲凉,“你跟我借一千块钱都要我写借条的时候,跟我谈过仁义吗?”
“我妈留给我的镯子,我戴都舍不得戴,为了给你那个‘公平’的家挣面子,我把它卖了的时候,你跟我谈过仁义吗?”
“张建国,仁义不是光用嘴说的。你用账本活了半辈子,那我今天,就让你也尝尝,活在别人账本里的滋味。”
这些话,像一颗颗子弹,打得张建国毫无还手之力。
他张着嘴,却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
因为她说的,全都是事实。
那些被他用“公平”和“原则”包裹起来的冷漠与自私,在这一刻,被血淋淋地撕开,暴露在空气里。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是张伟不放心,又折返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
“爸,妈,你们怎么了?”
张建国看到儿子,像是看到了救星,激动地指着赵秀兰。
“你看看你妈!你看看她做的好事!她要收我的陪护费!一小时五十!”
张伟也懵了,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最后目光落在了那张“价目表”上。
“妈,这……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跟爸开玩笑的吧?”
赵秀alaram摇摇头。
“我没开玩笑。你爸喜欢明算账,我就跟他明算账。”
“妈!”张伟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爸还病着呢!你怎么能……”
“我怎么不能?”赵秀兰打断了儿子的话,她的目光依然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小伟,这件事你别管。这是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
她转向张建国,语气恢复了之前的冷静。
“就这么定了。你要是觉得贵,也可以不请我。外面有专业的护工,你可以问问价钱,比较一下。”
“当然,请了外人,人家可不会像我一样,还愿意让你赊账,出院再结。”
说完,她拿起那个只动了一口的粥碗。
“这碗粥,二十块。你还没付钱。你要是不吃,就算了。你要是吃,吃完我就记在账上。”
张建国看着那碗粥,又看看赵秀alaram那张没有丝毫感情的脸。
他只觉得一股气血往上冲,眼前一阵发黑。
羞辱。
这是他这辈子都未曾尝过的,极致的羞辱。
他用他建立的规则,被将了一军,死死地。
“你……你……”
他“你”了半天,最后,一口气没上来,头一歪,又晕了过去。
监护仪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
张伟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冲出去喊医生。
病房里顿时人仰马翻。
而赵秀兰,就站在一片混乱的中央。
她手里端着那碗慢慢变凉的粥,看着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丈夫。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只是在医生和护士冲进来的时候,她默默地退到墙角,拿出自己的那个小本子。
翻开新的一页,写下了第一笔账:
“4月12日,下午三点至晚上八点,陪护五小时。共计二百五十元。”
第五章 旁观者
张建国被抢救了回来。
人是清醒了,但精神头,像是被抽走了。
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
张伟急得团团转,劝完爸爸劝妈妈。
“爸,你就当妈跟你开个玩笑,服个软,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张建国把头转向墙壁,不理他。
“妈,爸都这样了,你就别跟他置气了,行吗?钱我来出!你们别这样,我看着难受。”
赵秀兰正在用湿毛巾给张建国擦脸。
她的动作很标准,很程序化,就像医院里那些受过培训的护工。
“小伟,我说了,这事你别管。”
她一边擦,一边头也不抬地说:“他不是跟我置气,他是跟他自己定的规矩置气。”
“还有,这个钱,必须他自己出。你出了,就没意义了。”
张伟彻底没辙了。
他感觉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战场。
而他,连劝架的资格都没有。
赵秀alaram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
她每天准时来到医院,带上她的两个账本。
一个是她自己的小本子,记录“收入”。
另一个是她新买的硬皮本,专门给张建国记“支出”。
她把每天的开销都记在上面。
今天买了两个苹果,八块六。
今天打开水,五毛。
今天给他擦了一次身子,十块。
每记一笔,她都会把账本和相应的发票,放在张建国的床头,让他“过目”。
张建国一开始还气得把账本扫到地上。
赵秀兰也不生气,弯腰捡起来,掸掉灰,重新放回他床头。
“东西摔坏了,也要记在账上的。”她淡淡地说。
几次之后,张建国也就不摔了。
他就那么躺着,看着那个账本越记越厚,数字越累越大。
他感觉自己不是在住院,而是在坐牢。
一个用金钱和数字堆砌起来的,无形的牢笼。
而赵秀alaram,就是那个冷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狱卒。
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按时喂饭,按时喂药,按时翻身,按时擦洗。
医生护士查房,都夸她是模范家属。
“张师傅,你可真有福气,你爱人把你照顾得太好了,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床铺也干干净净的。”
每当这时,张建国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他有福气?
他情愿请一个骂骂咧咧的护工,也比对着这张“移动的价目表”要强。
他开始仔细观察病房里的其他人。
隔壁床住着一个同样是脑梗的老大爷。
他老伴每天乐呵呵地陪着他,一口一个“老头子”地叫着。
吃饭的时候,老太太会先吹凉了,自己尝一口,不烫了,再喂到老头子嘴里。
喂完了,还会拿出纸巾,仔仔細細地给他擦嘴。
那动作,自然得像呼吸一样。
有时候,老头子发脾气,骂骂咧咧的。
老太太也不生气,就拍拍他的手,哄小孩一样说:“好了好了,不气了,气坏了身子,谁陪我回家呀?”
张建国看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涩。
他也吃饭。
赵秀兰把饭端过来,用勺子舀起来,就直接往他嘴里送。
不试温度,也不说话。
他要是吃慢了,她就端着碗,面无表情地等着。
他偶尔被烫到,或者呛到,她也只是递过一张纸巾,然后在本子上记下:纸巾,一毛。
这种对比,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张建国的心。
他引以为傲的“公平”,在隔壁床那种黏糊糊、不算计的“糊涂账”面前,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冰冷。
很快,他老婆按小时收费照顾他的事,就在住院部传开了。
起初是邻居李婶来探病。
李婶是个热心肠,也是个大喇叭。
她看到赵秀兰正拿着小本子在记账,好奇地问了一句。
赵秀兰也没瞒着,实话实说了。
李婶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她走后不到半天,整个楼层的病友和家属,看他们夫妻俩的眼神都变了。
有好奇,有鄙夷,有同情。
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
“听说了吗?三床那个,他老婆照顾他,一小时五十块呢!”
“真的假的?这还是夫妻吗?”
“嗨,听说他家一直AA制,这老头子自己作的!”
这些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飞进张建国的耳朵里。
他一辈子都要强,好面子。
现在,他感觉自己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供人参观。
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他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着这几十年来的事。
他想起儿子小时候,发高烧,赵秀兰背着儿子跑了三条街去医院,回来累得瘫在地上。而他,第二天早上,把打车的钱和医药费算出来,让赵秀兰承担一半。
他想起赵秀兰的母亲去世,她想回娘家多待几天,他却说,家里的伙食费不能因为她不在就停了,她那份还是要照交。
他想起有一年过年,赵秀兰看中一件红色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满眼都是喜欢。他看了一眼价签,说:“你自己的钱,想买就买,别指望我给你报销。”最后,赵秀兰还是把衣服放下了。
一件件,一桩桩。
以前他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那么刺心。
他一直以为,他在建立一种先进、文明的家庭关系。
现在他才发现,他只是在用一把叫“公平”的尺子,一寸一寸地,丈量着彼此的感情,直到把所有的温情都量没了。
他躺在床上,第一次,感觉到了孤独。
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彻骨的孤独。
他偷偷地哭了。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深夜的病房里,把头埋在被子里,像个孩子一样,无声地抽泣。
眼泪流下来,打湿了枕头。
枕头套是赵秀alaram昨天刚换的,还带着阳光和肥皂的味道。
他忽然很想跟她说说话。
不是谈钱,不是谈账。
就想跟她说说,隔壁床的那个老太太,今天又给她老头子讲了个笑话。
可是,他一转头,就看到赵秀兰睡在旁边的折叠床上,背对着他。
她的背影,在清冷的月光下,显得那么笔直,又那么遥远。
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是他亲手挖的。
第六章 撕碎的账
张建国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出院那天,张伟来办手续。
看着账单上那一长串数字,张伟眉头都没皱一下,直接刷了卡。
张建国看着儿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他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大半,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回到家,赵秀兰把窗户都打开通风。
阳光照进这个一尘不染的屋子,却驱不散那份压抑的沉默。
张伟把父亲扶到沙发上坐好,又去厨房帮母亲收拾东西。
“妈,这事……就算了吧?”他在厨房里小声地对赵秀兰说。
赵秀兰正在洗手,水流哗哗地响。
“还没完。”
她关掉水,擦干手,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那个新买的硬皮账本。
她走到客厅,走到张建国面前。
张伟跟在她身后,一脸紧张。
赵秀alaram把账本放在张建国面前的茶几上。
“出院了,我们该把账结一下了。”
张建国浑身一震,缓缓地抬起头,看着她。
赵秀兰翻开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住院三十天,总共七百二十个小时。”
“日间陪护三百六十小时,一万八千块。”
“夜间陪护三百六十小时,两万一千六百块。”
“餐费,总计八百六十四块五毛。”
“其他护理服务,二百一十次,两千一百块。”
“总计,四万两千五百六十四块五毛。”
她念得很清晰,像个专业的会计,在做最后的年终总结。
每念一个数字,张建国的脸色就白一分。
张伟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
“妈……”
赵秀兰抬手制止了他。
她看着张建国,继续说:“这是我这一个月,应得的。”
张建国看着茶几上那个账本,和他自己那个牛皮账本并排放在一起。
两本账,像两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张伟都以为他要再次发病。
然后,他颤抖着,伸出那只还算灵活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口袋。
他从里面掏出钱包。
他的手抖得厉害,钱包打开了好几次才成功。
他从里面,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密码是……我生日。”
他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一样。
他把卡推向赵秀兰,眼睛却不敢看她,只是死死地盯着茶几上那两本账本。
那一刻,他放弃了所有的挣扎和辩解。
他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输给了他自己建立了一辈子的规则。
赵秀alaram没有去接那张银行卡。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看着这个和她生活了半辈子的男人,此刻像一个被宣判了刑罚的犯人,低着头,等待着最后的执行。
忽然,她伸出手,拿起了那个记满了她“收入”的硬皮本。
在张建国和张伟惊讶的目光中,她“撕拉”一声,把账本从中间撕成了两半。
然后,她又把那两半合在一起,“撕拉”一声,撕成了四半。
她一下,一下地撕着。
没有愤怒,也没有快意。
只有一种仪式般的平静。
最后,她把那堆碎纸,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客厅里,只剩下父子俩粗重的呼吸声。
“建国,”赵秀alaram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夫妻不是合伙人,家不是股份公司。”
“这一个月,我照顾你,不是为了挣你这四万块钱。”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被自己最亲的人,用钱来衡量是什么滋味。”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为你做的那些事,如果都标上价,会是一个你付不起的数目。”
“钱,我一分都不要。”
她的目光,扫过茶几上那个完好无损的牛皮账本。
“我只要,这个家,以后别再有账本了。”
说完,她转身走进了厨房。
没过多久,厨房里传来了切菜的声音。
笃,笃,笃。
一声一声,规律而安稳。
张建国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像。
他缓缓地,缓缓地转过头,看着厨房里那个忙碌的背影。
那个背影,他看了几十年,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影子。
可今天,他却觉得,自己是第一次,真正看懂了她。
眼泪,毫无预兆地从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滑落。
无声无息,却滚烫得灼人。
他伸出手,拿起自己的那个牛皮账本。
那个他珍视了半辈子,以为是自己人生信条的账本。
他用尽全身力气,想把它也撕掉。
可是,他病后的手,没有力气。
他试了几次,都只是把封面弄得更皱了一些。
最后,他放弃了。
他把账本,扔进了脚下的垃圾桶。
和那一堆碎纸,扔在了一起。
晚上,一家三口,三十年来第一次,吃了一顿没有算账的晚饭。
饭桌上很安静。
张建国默默地吃着饭。
吃到一半,他用自己那只颤抖的手,夹起一块他从不动筷的红烧肉,颤巍巍地,放进了赵秀兰的碗里。
赵秀兰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把肉夹回去。
她只是低下头,把那块肉,和着米饭,一起吃了下去。
夜深了。
赵秀兰躺在床上,听着身边张建国沉重而平稳的呼吸声。
她知道,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但她也知道,从明天起,有些东西,会不一样了。
那个摆在客厅电视柜和墙壁夹缝里的饼干盒,她明天会把它拿出来,扔掉。
还有她那个巴掌大的小账本。
也该扔了。
她想,明天,或许会是个好天气。
注册公司是实现您创业梦想的重要一步,它为您提供了更多的成功机会和发展空间。通过上文关于陪护费怎么做账的相关信息,主页相信你已经得到许多的启发,也明白类似这种问题的应当如何解决了,假如你要了解其它的相关信息,请点击主页的其他页面。